宋朝伪史:谢家福的伪书宇宙
作者:齐秋
提起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你会想起什么?
很多人会痛心疾首地告诉你何为靖康耻:金人兵临汴京城下,向宋朝索要巨额财富,宋人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就将昔日养尊处优的公主,比如宋徽宗的女儿赵福金、赵金姑、赵多富……以及众多皇家宗女、宗妇,“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作价抵扣给金人。而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后,他们的后宫妃嫔都被金人投入一个叫洗衣院的地方,金人王子贵族时不时去洗衣院挑选……
这些可称广为人知的宋朝悲惨故事,出自所谓南宋确庵、耐庵编撰的《靖康稗史》七种,是真的吗?
提起元朝初年的异族压迫,你会想起什么?
比如所谓元初实行甲主制度,“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甚至“花烛之夕,甲主踞之”。
出自所谓宋末元初苏州遗民徐大焯《烬余录》的记载,这是真的吗?
提起明末李自成起义打进北京城、吴三桂降清,也是大家熟悉的真实历史。那么如果有人说其中的细节,比如说李自成进北京城后忙着选宫女开后宫,“番僧汤若望”还给他进献春药,并且他还下这么一道旨意:
“发伪诏云:‘投顺官心挂两朝,昨已吊取并无忠心之家眷入宫,所有授职各官,均须将亲女或亲姊妹、妻、媳一人来献。入选官、听选官未经选女入宫,曾经幸御者,不准选授。犯赃、无用官家眷尽行入宫,钦哉。’”
而彼时吴三桂连写好几封信给父亲,每一封都忙着问询“陈妾安否”,一面“向清国借兵”,一面表示可以投降李自成,“但求将陈妾、太子两人送来”,否则就要与清兵一起长驱直入。
这些细节只见于所谓明末宫廷太监王永章写《甲申日记》,是真的吗?
太平天国时,颁发了不少诏书,实行各种新奇制度。如果有人说太平天国“伪分天下为二十四省”,并且“开苏州为苏福省,视天京例,谓将来作陪京”。
出自谢家福编辑的《燐血丛抄》,这是真的吗?
揭晓答案:以上这些历史的细节,都是假的。
这些“史料”,统统出自一位晚清士人的手笔,以一己之力塑造了纵贯宋元明清的伪书宇宙。
多面孔的谢家福
晚清苏州乡绅谢家福(1847—1896),应试名家树,字绥之、锐止,号望炊、锐庵、兰阶主人、桃园主人、春草吟庐主人等,在中国电报史、慈善史的书写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谢家福出身慈善世家,光绪初年“丁戊奇荒”时,他亲赴山东救灾,组织义赈,受洋务大员青眼,在洋务运动里,他参与筹办上海电报分局、苏州电报分局,是中国电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而在这些开明进步的表象之外,谢家福还有更多面孔。
清末民初著名小说《孽海花》里,有一位苏州的妓院常客“谢介福”,字“山芝”,雅号“大善士”,自然是影射谢家福。
身为妓院常客的大善士,在光绪初年赴山东赈灾时就喜欢看《宋史》为消遣。当谢家福在经历了义赈辛劳、洋务操劳之后,他回到苏州老家,打造出了多部“史籍”,时代跨度从两宋之交到宋末元初到明末到清末,记载了众多宋元明清历代世人从未知晓的历史细节。
编故事,对文人来说并非难事。谢家福初次出手,就是为父亲编造慈善故事。
谢家福的父亲谢元庆,字肇亨,又字蕙庭,是苏州著名善人。谢元庆死后,儿子谢家福给父亲写了个行状,说道光十一年(1831):
“江北水患,灾民麇集,府君(指谢元庆)与韩公桂舲、潘公功甫、潘公梅溪诸君集赀设厂留养,今闽抚宝应王公凯泰时在灾民中,府君觇其不凡,言于诸君,各厚助之。”
“王公凯泰”指王凯泰(1823—1875),江苏宝应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至福建巡抚,卒赠太子少保,谥文勤。
俞樾对这个慧眼识人的救助故事表示了极大的疑问:
“余谓此事未足信。闽抚王文勤公,余亲家翁也,知之最详。公生于道光癸未,至辛卯才九岁耳,必不能以一身就食江南,必其家长老挈之而来。乃是时其家初无变故,余撰文勤神道碑,即据其子儒卿等所撰行状,言公年十有一,四子书十三经皆卒读,其父赠资政公亲为讲授大义,然则文勤幼时必无流离转徙之事。”
“辛卯壬辰间,文勤之父方在本籍赈饥,文勤何至身入苏州灾民厂也?潘顺之前辈及余莲村善士所撰谢公传均不载此事,不知行述中何以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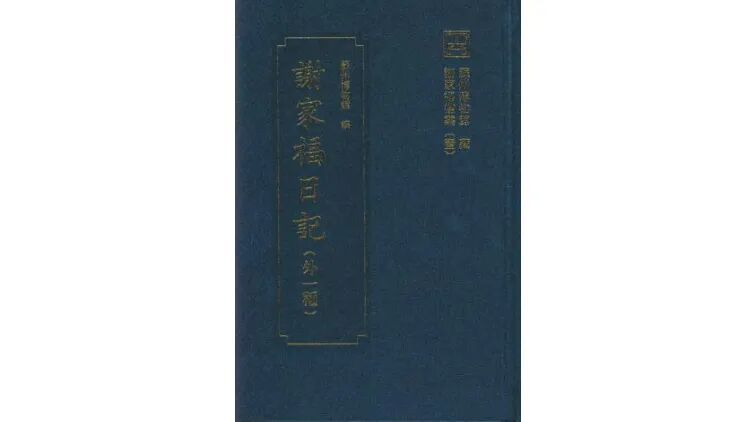
《谢家福日记》
作者:谢家福
编者:苏州博物馆
版本:文物出版社
2013年12月
王凯泰的神道碑就是俞樾写的,他是俞樾的亲家翁,“知之最详”,人家根本没有幼年流离失所,被谢蕙庭救助的故事。而且在谢蕙庭死后,当时其他人给他写的传记里都没有提到谢蕙庭救助王凯泰的事情,有,且仅有,谢家福说我爹做了这个好事。
除了为亡父编造的伪善事,几部从谢家福手里出现的历朝史籍,无一例外是从未见于历代记载的独家孤本。
比如所谓宋末元初苏州徐大焯所著《烬余录》,里边记录了所谓甲主制度。但这部书从元初到清末都没人知道,直到光绪年间谢家福拿出来。
《烬余录》全世界最早的两个版本都出自谢家福,一种是不全的,光绪十七年望炊楼刻本,此本是每页10行,每行24字的设计。这个版本是不全的,甲编缺失“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庙幸清河郡王张浚(其实是张俊,谢家福错成张浚)第,进奉筵目”。一种是全本的,谢家福送给藏书家丁丙的自家“桃坞五亩园”抄本。
刻本《烬余录》甲编里,杨家将故事之后有15行、一页半的空白。而后来的抄本《烬余录》里,填补了这处空白,增加的故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臣子宴请皇帝的宴席菜单。
这份菜单的真实历史记录,保存于宋末元初周密的《武林旧事》,题为“高宗幸张府节次略”。除了宴请宋高宗本人的具体流程,还有给跟随的大小官员的菜单,还有张俊在此次宴会上进献给宋高宗的宝物清单,最后还记载了宋高宗给张俊家族亲属推恩。
《烬余录》抄袭《武林旧事》这一节的时候,删减了宴会的步骤,只抄了给宋高宗的菜单,其他的都没抄。就是给宋高宗的菜单,也删了好几个步骤,修改了步骤名。比如《武林旧事》里记载有“下酒十五盏”,每一盏酒配两样菜品,合计30个。《烬余录》则改成“下酒三十味”,去掉酒盏,只抄30个菜名,还把“鳝鱼炒鲎”错成“鳝血炒鲎”,“青梅荷叶儿”和“雕花姜”两个菜品,错成“青梅”“荷叶姜”。把宴席流程里的“砌香咸酸”错成“砌香盐酸”,“脯腊”错成“脯肠”,漏抄了一个“肉腊”;“新椰子象牙板”错为“新椰子”,“香莲事件念珠”错为“香莲事件”,“葴杨梅”错为“杨梅”,“荔枝蓼花”错成“荔枝葵花”……等等。
真实的张俊宴请宋高宗菜单,出自周密记载。周密妻杨氏,是南宋七王之一和王杨存中的后代,又是宋理宗的表妹,周密因此得以了解皇室密辛,他笔下的相关文字记载是可以相信的。那么谢家福编造的所谓宋末遗民苏州街巷里的徐大焯是谁啊?
正因为《烬余录》实际出自清末,谢家福抄录这份菜单时,作为清朝人对宋朝诸多名词并不理解,随意删改,形成了现有文字。
《烬余录》里,屡屡出现一个叫“李山民”的人的故事,他在谢家福拿出来的另一部独家孤本“史籍”《靖康稗史》里,叫“李浩”。
《靖康稗史》七种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谢家福于光绪十七年(1891)购入《三朝北盟会编》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本,很巧,第二年,也就是光绪十八年(1892),谢家福便送给藏书家丁丙一部所谓从海外回流的《靖康稗史》抄录本。
《靖康稗史》里除了第一种《行程录》,剩下六种,在宋元明清历朝都没有任何记载,直到光绪十八年,这部书终于面世。
谢家福给《靖康稗史》安排了看似严谨的文本传播路线:
南宋末年成书——元初传入朝鲜——本土亡佚,在海外流传——不知何时传到日本——从日本回流中国本土,被谢家福“借”到。因为是借来的书,谢家福不能转送他人,于是找人抄录之后,把抄录本送给丁丙——非常完美,这样即使丁丙知道这些纸张、笔墨都是新的也不会怀疑。
至于谢家福“借”到的、从日本传回中国的原本呢?只存在于谢家福的嘴里,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见过。
我国古籍确实有一些本土失传、海外回流的,清末这种事情还不少,但并不适用于《靖康稗史》。
原因很简单:如果谢家福说的是真的,《靖康稗史》从宋末元初就传到朝鲜了,那么里边的文字,必须是宋朝原貌啊!事实呢?
《靖康稗史》收入的唯一真实史料《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全文抄袭《三朝北盟会编》袁祖安本的卷20。作为宋辽金史重要史料,南宋徐梦莘编撰的《三朝北盟会编》,有50多个明清时期的版本留存,其中卷20一整卷都是《行程录》,宣和七年许亢宗率领使团出使金国祝贺金太宗吴乞买登基,回到宋朝以后,使团里的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写了《行程录》,入金以后的行程一共有40程,后来分别收入南宋成书的《会编》和元朝成书的《大金国志》。但是,在这50多个版本的《会编》里,除了袁祖安本,这个行程录都是缺少部分行程文字的,没有第一、六、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程,只有袁祖安本《会编》里,这些行程都在,是完整的。
袁祖安本跋语写于光绪四年(1878),实际出版在光绪五年(1879),在整个《会编》传抄系统里,是非常独特的一部,它的编辑人员并非宋史学者,而且对原文随意改动,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谬误,被后来的学者们痛斥这一版《会编》还不如不面世。那么面对卷20不完整的行程,袁本的编辑怎么补全的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用《大金国志》补入缺失的行程。
元朝书商编撰的《大金国志》其中有一卷是这个行程录,四十程都在,但对其中文字有删改,与原始的《行程录》文字并不完全相同,与《会编》版本的文字也略有不同,是单独流传的系统,而袁祖安本《会编》的编辑,直接照抄《大金国志》。
于是,在袁祖安本《会编》里,宣和七年的宋朝官员钟邦直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第一程……南宋与契丹以此为界。”
一个北宋官员会在给朝廷写的报告里自称“南宋”?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个写法?因为元朝人编撰的《大金国志》收入的《行程录》是这么写的——元朝人可以这么写,你宋朝人自己也这么写?
又如第二十五程,《会编》各本皆只有“至没咄孛堇寨”以及对没咄、孛堇的解释。袁祖安本抄《大金国志》时,此处漏抄具体行程描述的47个字,《靖康稗史》里,自然也没有这段话。
其他错字写法,如“都辖”错为“都辐”、“习驭直”错为“习驭司”、“仪鸾司”错为“鸾仪司”、“泒水”错为“涿水”……等等,分开来看,在其他版本的《会编》里也偶有写错,但没有把这些全都写错了的,有,且只有袁祖安本都写错了,而这些错误又全都出现在光绪十八年谢家福拿出来的《靖康稗史》里。——这是宋人记宋事,从元初就流传海外,清末方才回流的“古籍”啊,怎么会出现光绪四年以后才会有的这些错字写法呢?
更为神奇的是,《靖康稗史》之《开封府状》里说宋徽宗有个女儿叫赵福金:
“福金帝姬……因邓珪传奉国相令旨,福金是皇子夫人位号,应送皇子寨中,以符名谶。”
“福金帝姬”指宋徽宗之女茂德帝姬,茂德是她的封号,她的本名并没有流传下来,“福金”之名仅见于《靖康稗史》。起这个名字,显然是要人理解成“福晋”,即清朝时皇室贵族妻子称号,目的是将她送给金国皇子,“以符名谶”。
但是,“福晋”为皇子夫人是清朝人的概念,宋金时期,金人的妻子没有这个称呼,贵族妻子封号也不这么叫。因此,真实历史上,无论宋人还是金人,并不会看到一个名叫“福金”的女人,联想到这个人应该做皇子的“福晋”。
以及,茂德帝姬的名字也不可能叫“福金”,因为宋朝宗室女性的命名与宗室男性一样,大体上按照固定联名字辈取名。比如宗女赵善意的父祖名字是仲忽—士珸—不慮—善意;宗女赵汝议的父亲叫赵善临,她的兄弟名字是汝谈、汝谠、汝训、汝诂,都是按照宗室联名字辈取名。
那么宋徽宗的女儿们,真实名字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他的儿子们名字是确定的:桓、柽、楷、楫、枢、杞、栩、棫、构、材、模、植、朴……则他的女儿们名字也必定有规律可循,绝不可能是什么福金、金奴、金姑、多富之类。

谢家福煞费苦心编出这些故事,是为了什么呢?
在《烬余录》和《靖康稗史》里,有一个相互印证的李山民李浩家族故事,在谢家福笔下,跟随两宋之交的战火,编织出忠臣李若水之子李浩的传奇:他被设定成李若水的儿子,和李若水一起出使。李若水殉国后,这个李浩进入二圣北狩的队伍,冒充宋徽宗的儿子,因为长得像宋徽宗第十八个儿子相国公赵梴,所以在建安郡王赵楧死后,被当成相国公赵梴。——不要问我这个因为所以怎么来的,《靖康稗史》里就这么写的。
而李浩冒充皇子,还被宋金双方都认可,宋徽宗认下这个假儿子,金人为他娶妻亡辽公主耶律氏,耶律氏死后,又为他娶妻韩氏,生子李茂实。绍兴十二年(1142)韦太后返回南宋的时候,李浩带着儿子一起跟着韦太后回到南宋。之后,李浩结合自己的经历,并摘取宋金双方的笔记,写成《靖康稗史》里的《呻吟语》。他死后,儿子李茂实在隆兴二年(1164)整理父亲遗作,南宋末年被耐庵整理成《靖康稗史》。
李浩曾经将自己写的书献给南宋朝廷,受到打击,还好韦太后维护他,他才得以脱身,从此隐居在苏州桃花坞——这就和谢家福的五亩园历史连起来了。
一切的一切,缘起可能只是为了谢家福苦心经营的苏州桃花坞五亩园。为这片园林构建辉煌谱系,他陆续“贡献”了从汉朝到清朝的“独家史料”。
谢家福于光绪十四年(1888)购入苏州桃花坞地方,命名为五亩园,大兴土木,打造成谢氏名胜。桃花坞名气在明朝因唐寅而出名,谢家福却不甘心历史渊源只追溯到明朝。苏州地方一直人文繁盛,南宋时期著名的方志有范成大编的《吴郡志》,但这部《吴郡志》里并没有涉及谢家福五亩园的故事,求人不如求己,谢家福推出了《五亩园小志》。
《五亩园小志》的序言称谢家福手里曾有过一部五亩园“旧志”,谢家福根据旧志,并加上自己找到的“史料”如《烬余录》,完成了这部新志。——至于“旧志”,和《靖康稗史》从海外回流的原书一样,只存在于谢家福嘴里。
谢家福把桃花坞五亩园的历史,上追到汉朝,实际记载上追到北宋梅宣义、章楶,称“熙宁绍圣间园林水石之胜甲吴中”。
但是为什么南宋范成大编《吴郡志》没有记载呢?因为“建炎初兀术蹂躏”,“范文穆公(范成大)在南宋时为《吴郡志》,已不知五亩园所在矣”。
又为什么元明几百年也不知名呢?“伯颜南下”“淮张窃据”,所以“元明两代纪载阙如”。
又为什么清朝前期也没人知道呢?“国朝承平二百余年,而宣义碑记出自土中,旋毁于庚申之变”。因此,谢家福“惧其久而复湮也,为《五亩园小志》。”
——所谓北宋碑记在清朝乾嘉年间出土的故事,与谢家福同乡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曾提出疑问:
“《五亩园小志》一册,谢绥之所辑,后为《志余》,则绥翁与吴江凌磬笙明经同述,亟披阅之。汉时为张长史植桑地,未知何据。……又云乾嘉间,有梅姓自江右访祖墓于园西,掘地得碑记十余种,皆宋贤撰著。乾嘉距今不过百余年耳,何以无片石存诟?”
叶昌炽对金石很有研究,苏州又向来是人文之地,如果五亩园在汉朝就有存在感,不会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记得,要到清末才被谢家福写出来。而如果真的在乾隆嘉庆年间出土过十余种宋人碑记,苏州当地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记载,要等谢家福编出《五亩园小志》才知道有这回事。
《五亩园小志》序言还提到内文多处使用的《烬余录》不见于历代书目,反而出现于庚申兵燹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是老天保佑的结果。而在有了《烬余录》这本书之后:
“桃坞七百余年之事实粗具于此”。
对于谢家福,他拿出来的诸本“史籍”就是这么个作用。为了五亩园,推出《五亩园小志》,又用《烬余录》填补缺失的历史记载;为了证明《烬余录》,他又拿出《靖康稗史》佐证,环环相扣,构成了清末谢家福伪书宇宙。
至于为什么宋元明清历代都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史料会出自谢家福之手——
《五亩园小志》记载有个丈人峰,相关文字就出自《烬余录》,但谢家福却说:
“予为《桃坞百咏》时仅见《志余》,尚未知桃坞实赅大云乡全境,报恩寺、承天寺、神仙庙等尽在界内。当时万不得已将毫无故实之轩亭率凑而成。早知有此许多好题目,则如丈人峰等断断不呕心血也。”
——如果是真实的宋末元初史料,谢家福会说“毫无故实”“呕心血”吗?这是一个造假者露出的马脚。



